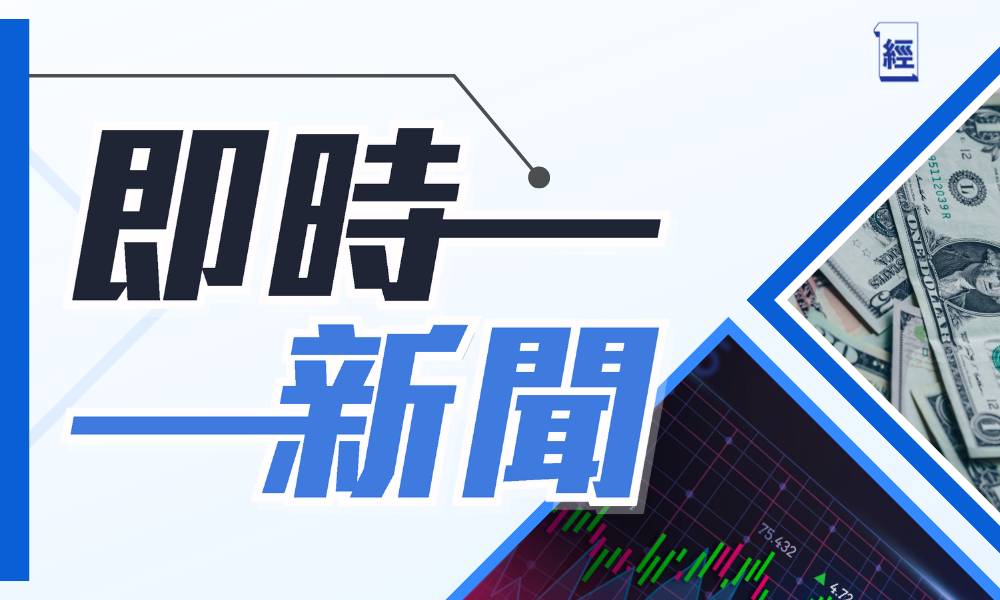特朗普關稅|特朗普「關稅核彈」衝擊全球:歷史上最早19世紀已經有關稅政策
特朗普關稅|歷史前例:美國高關稅時期的經驗教訓
美國歷史上多次實施高關稅政策,效果與後果各異,對當前特朗普政策有重要啟示:在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推出「對等關稅計劃」,標誌著關稅戰2025的開端。這項政策對進口商品徵收10%基準關稅,並對中國、歐盟、日本等國加徵更高稅率,意在縮減貿易逆差並重振美國製造業。然而,美國歷史上多次實施高關稅政策的經驗顯示,其結果往往利弊參半,對當前關稅戰2025提供深刻啟示。從19世紀的南北矛盾到1930年代的大蕭條,再到1970年代的通脹危機,這些歷史前例揭示了高關稅的潛在風險與機遇。
1. 19世紀初期至南北戰爭前:保護北方工業,激化南北矛盾
背景:19世紀初,美國聯邦政府通過高關稅(如1828年《可憎關稅法》,平均關稅達45%)保護北方新興工業,促進紡織與製造業發展。
影響:
北方受益:工業化加速,北方製造業在1860年前增長約3倍。
南方受損:南方農業依賴出口棉花至英國,英國報復性關稅導致棉花出口銳減,經濟損失約20%。
政治後果:高關稅成為南北矛盾核心議題之一,南方認為聯邦政策偏袒北方,加劇分裂,最終成為南北戰爭(1861-1865)的遠因之一。
啟示:關稅政策可能加劇國內經濟與政治分歧,需平衡不同地區利益。
2. 1930年史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加劇大蕭條
背景:1930年,胡佛總統簽署《史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將進口商品平均關稅提高至40%,試圖保護美國農工業免受大蕭條(1929年開始)衝擊。
影響:
報復性關稅:超過25個國家對美國商品加徵懲罰性關稅,如加拿大對美出口徵收50%關稅。
貿易萎縮:1930-1932年,全球貿易量下降約30%,美國出口總額跌超60%(從52億美元降至20億美元)。
經濟惡化:經濟學家廣泛認為該法案加劇大蕭條,美國GDP 1933年較1929年下跌近30%,失業率升至25%。
啟示:高關稅可能引發全球報復,導致貿易與經濟雙輸,特別是在經濟低迷時期。
3. 1970年代尼克遜政府:臨時關稅與通脹危機
背景:1971年,尼克遜政府因經常帳赤字與美元地位不穩(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實施「臨時進口附加稅」(10%關稅)與貿易限制,試圖削減貿易逆差與促進就業。
影響:
短期效果:汽車與鋼鐵等產業短期受益,1971-1972年就業增長約2%。
中長期後果:關稅推高進口成本,1973年美國通脹率升至6.2%,1974年達11%,進入「停滯型通脹」(stagflation)時期。貿易夥伴(如日本)報復性措施加劇矛盾。
啟示:關稅可能帶來短期收益,但中長期可能引發通脹與貿易緊張。
4. 列根時代:從關稅轉向談判
背景:1980年代,列根政府初期延續保護主義,但後期轉向「自願出口限制協議」(VERs)與匯率談判(如1985年《廣場協議》),避免單邊加稅。
影響:
VERs效果:日本自願限制汽車出口,美國汽車業1985-1988年利潤增長約15%。
匯率調整:《廣場協議》使美元貶值約50%,促進美國出口,但也導致日本經濟泡沫化(1990年代初崩潰)。
啟示:談判與多邊協調比單邊關稅更能實現貿易平衡,且減少報復風險。
特朗普關稅|當前關稅與歷史的差異: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挑戰
特朗普的「關稅核彈」與歷史高關稅時期有本質不同,影響更為複雜:
供應鏈整合:
1930年代,全球供應鏈尚未高度整合,關稅主要影響最終產品。
2025年,產品設計、生產、組裝跨國進行(如iPhone涉及中國、台灣、日本等多地),關稅不僅提高進口成本,還衝擊美國製造商的零組件供應與出口競爭力。
例如,美國汽車業依賴墨西哥零件(2024年進口額約1000億美元),若對墨西哥徵收高關稅,美國汽車價格可能上漲10%-15%。
金融市場流動性:
1930年代金本位制下,資本流動有限,企業難以避險。
2025年,金融市場高度流通(全球外匯日交易量約7.5萬億美元),企業可通過轉移生產基地(如越南、印度)或金融工具(如期貨對沖)降低風險,但也可能加劇資本市場震盪(標普500已跌10.5%)。
政策性質:
特朗普的關稅被稱為「逆差懲罰稅」,針對貿易逆差與關稅差異(如中國對美農產品徵收25%,美國僅3%),更具指向性,而非單純保護主義。
但其「普遍性加稅」涵蓋原物料與中間產品,可能削弱美國製造業靈活性,與凱因斯學派建議(關稅應針對最終產品)相悖。
特朗普關稅|對各國的影響與因應
特朗普關稅衝擊全球貿易,影響與因應如下:
影響:
貿易額衝擊:彭博社估計,關稅影響超1.6萬億美元(約12.4萬億港幣)全球貿易,波及歐盟、日本、韓國、墨西哥、台灣等。
報復性措施:中國對美加徵34%關稅,歐盟考慮調整碳邊境稅,加拿大對美徵收25%關稅,全球貿易戰風險上升。
通脹與停滯風險:關稅推高進口成本,美國通脹可能升至5%,若經濟增長放緩(高盛預測2025年美國GDP增長1.8%),可能進入「停滯型通脹」危機。
因應:
中國:可能通過刺激內需(2024年消費佔GDP僅38%)或與特朗普談判應對,但內需政策效果有限。
歐盟:可能與中國、越南形成「非美國貿易集團」,但需防範中國商品傾銷。
香港:維持自由港定位,吸引美國與內地旅客購物,但需應對外貿與物流業衝擊。
區域協定:RCEP與CPTPP可能加速擴張,繞開美國推進自由貿易。
特朗普關稅|核心資料列表
| 項目 | 詳情 |
|---|---|
| 關稅稅率 | 中國54%、歐盟20%、日本24%、韓國25%、台灣32%、越南46%、柬埔寨49% |
| 貿易影響 | 影響超1.6萬億美元(約12.4萬億港幣)全球貿易,WTO估計2025年貿易量減1% |
| 歷史教訓 | 1930年史穆特-霍利法案致全球貿易跌30%,美國出口跌60%,加劇大蕭條 |
| 美國貿易逆差 | 2024年達1.2萬億美元,中國順差約4000億美元 |
| 市場反應 | 標普500跌10.5%,納斯達克跌11.4%,全球富豪財富損失超5000億美元(約38873億港幣) |
特朗普關稅|分析:關稅核彈的長期影響
特朗普關稅不會重現1930年代大蕭條,但可能帶來以下影響:
短期震盪:資本市場動盪(標普500已跌10.5%),通脹加劇,美國消費者與企業承壓。
中長期風險:若關稅戰升級,可能引發「停滯型通脹」,全球供應鏈重組成本上升。
政策調整可能:特朗普可能從「普遍性加稅」轉向「針對性加稅」,聚焦最終產品與戰略產業(如半導體),以減少對美國製造業的傷害。
特朗普關稅|展望:全球貿易新格局
特朗普關稅挑戰多邊貿易體系,但自由貿易不會終結。區域協定(如RCEP、CPTPP)將加速發展,非美國貿易集團可能形成。美國可能通過談判重塑對其有利的貿易結構,但其全球貿易中心地位或下降。香港等經濟體需靈活應對,抓住自由港機遇的同時,防範經濟疲弱與通脹風險。
免責聲明:本專頁刊載的所有投資分析技巧,只可作參考用途。市場瞬息萬變,讀者在作出投資決定前理應審慎,並主動掌握市場最新狀況。若不幸招致任何損失,概與本刊及相關作者無關。而本集團旗下網站或社交平台的網誌內容及觀點,僅屬筆者個人意見,與新傳媒立場無關。本集團旗下網站對因上述人士張貼之資訊內容所帶來之損失或損害概不負責。